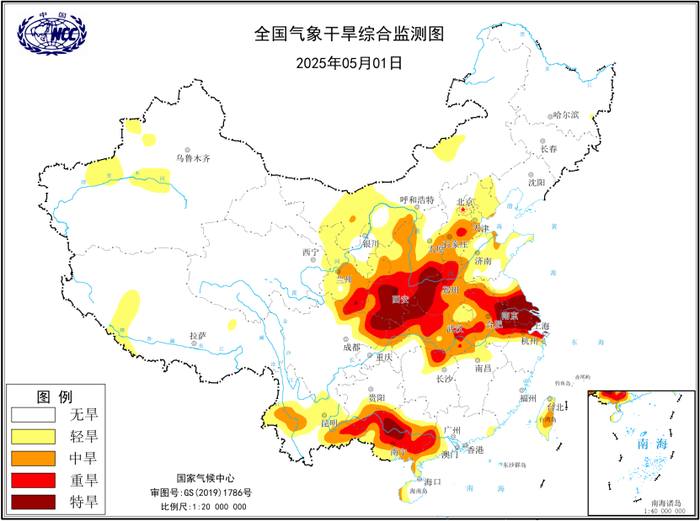八戒八戒免费影院:大 日 风 思-“不给好评”的青年社死网络,网约车司机活在你我眼前


徐楚谦|文
4 月 11 日,何同学分享自己处理网约车司机索要好评的经历引发争议,瞬间冲上微博热搜第一。他发文道,以前网约车司机让我给个好评我都会给,但现在我会直接说 " 抱歉我不想打 ",并且认为这是讨好型人格锻炼勇气的方式,由此引发全网反感。大多网友认为这是何同学本人作为千万粉丝 UP 主隐藏在言语背后的傲慢与偏执,表面上他拒绝了司机好评的请求—多么个人化的、微小的生活选择,可当世俗意义上客观的幸福者碾过更不幸之人的生活细节被高调声张时,却能如此撼动事件表皮下强弱逻辑的神经,并再度引出 " 幸福者退让 " 的探讨。
" 幸福者退让论 " 主张在社会结构不公、权力分配不均时,较为 " 幸福 " 的个体应主动展现出更大的理解与退让,以弥补系统性的不平等,或是作为自保、规避嫉妒与抱负的手段。那么在这样的逻辑下,何同学作为一条广告上百万营收的大网红,在面对一位平凡的、为生计奔波的网约车司机时,自然被隐形地期待着承担更多的情绪体谅社会责任,哪怕只是通过一个小小的 " 口头答应 " 来缓解对方的生存焦虑。
但何同学选择了拒绝。他到底在拒绝什么呢?个人成长和社会公平的冲突需要个人权利的让渡去平衡吗?
好评是表,失衡是里。何同学的个体权利维护思维无疑是将打网约车的生活场景当作试验场,在小人物上操刀实验,试图落地每个人都有权设定自己的权利情绪边界的实验目标;与此同时,大部分网民遵循的却是结构性补偿逻辑,在社会资源极度不平等的现实中,客观意义上幸福者应当额外付出温柔与体谅来弥合阶层间的缝隙。于是,何同学的拒绝表现为个体抵抗结构性补偿的一种小小姿态,他不愿牺牲自己的幸福去承担超出自身应负责任的情绪劳动。而一旦这一瞬间被置于宏观社会期待之下,他的拒绝便被解读成了幸福者对弱势群体的漠视,甚至是对不公现实的无声助推。或许,在个体正义与结构补偿之间确实存在着难以调和的价值张力,但 " 幸福者退让论 ",是否真的应成为处事真理?
当我们将那句听来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箴言 " 幸福者退让 " 掰开、嚼碎之后,发现其中的善与慧,竟也带着几分陌生与尖利。我想在评判前发出四个疑惑。第一问,评价 " 幸福 " 的标准是什么?第二问," 退让 " 指的是什么?第三问,如何才能被称为智慧?第四问,善的标准何在?作用于谁?
首先,何同学是更幸福的吗?如果幸福被异化为房子车子票子和类似符号的话,或许是的,但这样用社会物质资源来粗暴划分 " 幸福 " 与 " 不幸福 ",忽略了人在巨型结构中的孤独、挣扎、脆弱,也无视了幸福本身的复杂性、流动性与时效性。搞不清谁更幸福的话,幸福者的前提也不攻自破,谁幸福谁退让也无法量化。
再者,如果 " 退让 " 是委曲求全、自我削减地讨好,那么合理性存疑,但真正的退让,不是被动的自我阉割满足对方,而应该是有尊严的理解。何同学扪心自问,到底是在锻炼勇气还是拿不会对自己产生威胁的人开刀?当然有许多人持有幸福者退让的信条,并举出外卖小哥因为被打差评而入室报复的案例。曾有山东路虎司机的逆行追尾大巴车,本该由她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但在情绪失控下迁怒于坚持原则不让道的男司机。而男司机的选择是即便被连续扇了十几个耳光、脸上血流满面却仍不还手,只因孩子正坐在后座。他的 " 退让 " 并不是软弱。在秩序失灵的小场景中,退让不再只是道德抉择,而是一种生存智慧。
可我们反过来比对,何同学面临的是这样的境遇吗?在不明确谁更幸福的前提下,在并非是退无可退的境遇中,在这个过程中,不存在直接的人身威胁、不可控的暴力风险、或对无辜第三方的保护义务。" 幸福者退让论 " 不是万能的,也不应该变成一种绑架。在一个正常、对等、非暴力的互动里,坚持边界的行为本身就是在尊重自己,也尊重对方。否则,所谓的 " 幸福者退让 ",就会被滥用成一种对个体心理健康的侵蚀、对道德绑架式的合理化,以及让结构性问题被个体的自我消耗所遮蔽的伪善。
那么,如何才能被称为 " 智慧 "?我认为,真正的智慧应该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以不抹杀个体尊严的前提中寻找更大的一方净地,让更多人得以自由舒展地呼吸。边沁提出 " 一切道德行为的评判标准在于:是否能够为最多数人带来最大程度的幸福。" 在人与人交往中,幸福不仅仅来源于自我得到满足和磨砺、打怪升级,更深的幸福感其实蕴藏于微小、善意、被理解、被接纳的瞬间,而网约车司机和外卖小哥笑着对你说出的 " 打个好评,谢谢啊 " 并非逼迫与强势地倾轧,仅仅是弹性空间里渴望被接纳的礼貌示好,我们不必用强弱逻辑那一套桎梏住人心的温存。这样的细微选择,才真正符合边沁主义中更完整、更复杂的最大幸福原则:不是简单的自我幸福与他人幸福的二元对抗,而是最大化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善意流动,也是智慧蕴于生活的终极呈现。
最后," 善 " 的标准何在?作用于谁?善从不该沦为某一方单方面负担的重物。不是何同学肩上不可背负的情绪价值之重,更不是广大 " 幸福者 " 面临看似不幸者时心底愧疚与恐惧的无底洞,真正的善必须是双向的——既体恤 " 弱势者 ",也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与边界。善的标准不是牺牲自己成全他人,不是无底线地揣测或承担他人的恶意。它应当是发出的一句追问,指向相关平台的强制性求好评措施,指向相关平台超负荷的时间管理机制,它应当作用于背后那条条看不见的糜烂规则的修补,让更多的人能够在不必互相侵蚀的前提下、不必牺牲自己的情绪与权利的条件下,呼吸自己的甘甜空气。如果善良只是用来弥补结构性失衡的裂缝,而不是推动结构性变革,那这份 " 善 " 是否是下坠的善?一种在表面温柔下裹挟着纵容与失语的善?那么不妨问问自己,我挑战结构了吗?我成为那个举着武器冲向风车的孤胆英雄了吗?我真的是在用善良流淌出艰苦生活中的甜吗?这还是我们想要的善行吗?
可是,论述到这里就够了吗?我发现背后真正的问题了,我看到那张看不见的网和背后附着的整体性不公了,做个风中拔剑呐喊的堂吉诃德、刺向更隐晦的结构链条上的锈迹就能完全挑明我们真正需要的善吗?